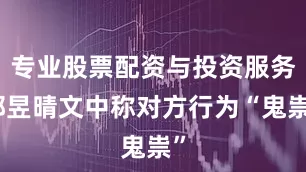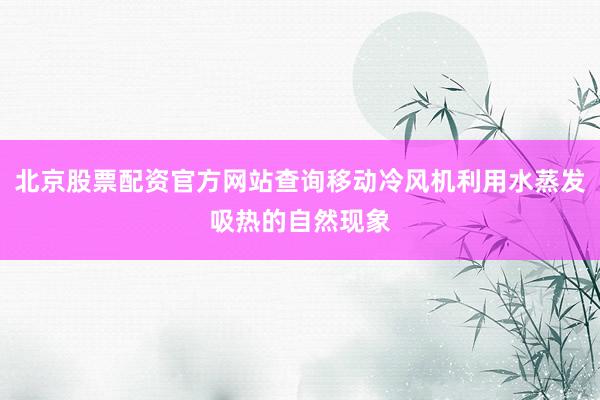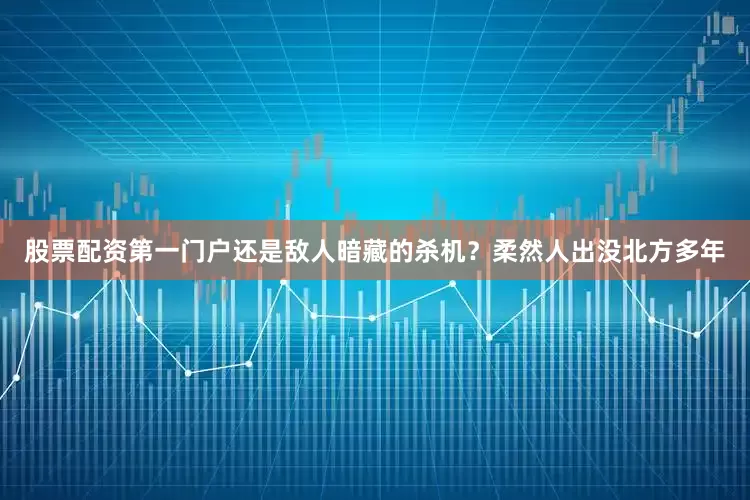
改写后的文章:
---
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北魏边军押送粮草途中,一头驴的耳朵突然不见了。将军扫了一眼,脸色顿时变得异常凝重,随即下令停队修筑一道墙。寒风刺骨,积雪厚重,敌骑如狼似虎,尽管如此,这道临时“水泥墙”最终成功阻挡了敌人数千人的猛攻。
那头驴耳的失踪,究竟是巧合,还是敌人暗藏的杀机?
柔然人出没北方多年,北魏早已深知他们骑兵的凶猛与狡猾——柔然骑兵不以宣战为常,来去迅猛,擅长打击敌人最脆弱的环节。
这一年,太武帝亲自领兵征战柔然,将主力军队远远调走。供给线一拉,就拉开了数百里之远,若是断了后勤线,前线将陷入绝境。因此,司马楚之这次押粮任务,关乎整军生死。他一向不出风头,容貌也并不出众,但太武帝非常信任他,曾说过:“此人能避大患。”
展开剩余88%三千士兵,二千辆粮车,押运着充足的粮草从北路出发。司马楚之能容忍一切,却唯独不能容忍——敌情不明,信息不畅。
第三天,天气骤然寒冷,雪花纷飞,密林中雾气弥漫,马队行进缓慢,前方骑兵警觉四周,眼睛不停地扫视。忽然,他们进入了一处洼地,四周被山坡环绕,直觉告诉他哪里不对劲,却又说不清。
就在这时,一头驴打了个响鼻,侧头看去,他瞬间发现——左耳不见了,根干净,仿佛被锋利的兵刃一刀割下。
他立刻勒住缰绳,跳下马来,跪在地上观察伤口,未见鲜血,说明被割的时间并不久远;也未见咬痕,排除了野兽的可能。地面上还有蹄印,一长一短,深深的陷入泥雪。
他微微皱眉,走向第二头驴,左耳同样不见了,第三头耳朵完整,第四头又缺耳。
不到十分钟,他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。
柔然的探马有一习惯,割敌畜耳作为暗号,传递“此地可劫”的信号。老套路,老方法,他们无需写纸条、悬挂旗语,一只驴耳就是入侵的宣言。
从那一刻起,司马楚之明白:敌人已来,柔然已经知晓这支粮队的位置,接下来就是进攻。
“停车,全军卸车,找柳树,砍下来,剥去树皮,编成墙。”
他的声音不大,但那种坚决的语气犹如铁锤敲进耳中。
“拿水,把墙泼上,冻住它。”
士兵们一时愣住了,押粮本是辛苦活,谁料到走着走着却得筑墙。有人低声嘀咕:“这……是不是有点过了?”
没有人敢高声说话,大家看到司马楚之仍未脱甲,亲自拿水桶,踩着冰碴,一趟趟往回走,没停歇,连夜忙碌。
那晚,气温降至零下十五度,水洒上去不到三十秒就结成了一层薄霜,三层五层加上去,柳条墙瞬间变成了坚硬的冰墙,触感冰冷刺骨,手指一碰便脱皮。
百余人轮换着干,整整一夜,终于在山口周围筑起了三十丈长的冰墙,两侧封死,中间仅留一个狭窄的门口。
天边微亮,雾气尚未散去,远方传来马蹄声,一队身披皮裘、头戴铁盔的骑兵渐渐显现。
司马楚之站在冰墙后面,静静观察,只淡淡地说了一句:“来了。”
柔然骑兵素以速度和冲击力著称,冲在前线的他们习惯一举突破。然而,他们最害怕的两样东西是:泥泞和冰雪。
柔然骑兵愣住了,他们无法相信有人竟然会用这种方式布防。
前锋试图接近,马蹄一滑,连人带马摔倒在地,后续骑兵连忙跟上,却也因滑倒而翻成一团。
第二波敌人换了策略,用火攻。
他们拿来了火盆和油壶,一点火往冰墙泼去,想要用火融化冰层。
然而,火焰刚刚燃起不到两柱香的时间,冰层突然发出一声巨响,瞬间炸裂,火焰反被冻了回去,根本无法继续燃烧。
他们慌了神,司马楚之冷眼旁观,随即一声令下:“放箭!”
箭雨如暴风骤雨,连射三轮,目标并非人,而是地面,退兵的路径被箭雨封死。敌人想撤退,却无法站稳脚跟。
经过三波冲击,敌军虽然伤亡不大,但士气彻底崩溃。
柔然军的指挥旗帜撤了,主帅随之露面,竟是封沓——曾是北魏的叛将,此人原是西北校尉,背叛北魏后投降柔然。
他站在冰墙前,冷冷地吐出一句话:“不该教他们这些……”
是的,他教的正是司马楚之的智慧。
他教了敌人如何割耳为信号,却忘了,敌人中也有人能够看懂这信号。
柔然撤退的那天,气温更冷了。司马楚之留下了冰墙,并带领队伍继续前行。
他知道,敌人不会轻易放弃,下一次,他们必定会更加谨慎。
然而,司马楚之也知道,若再次遭遇,“这道墙,还能再筑。”
发布于:天津市配资门户难简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